|
第一辑 亲情无边
麦口
农历一过了五月半,就临近麦口了。麦口不是个确定的词,它只是老家父老乡亲代代相传的一个口语,从字面上看,该是收麦当口的意思。这是我想当然的一种解释,不过有时想当然是会出错的。就像有位作家,曾向一家杂志推荐过汪曾祺的作品,那篇文章里有“秦邮八景”的字样。作家知道汪先生是高邮人,心想一定是先生的笔误,就想当然的给改成了“高邮八景”,结果闹出了笑话。不过还好,我的这种想当然的解释就算是出了错,也无伤大雅。
有点跑题了,重新回头写我的麦口。在我成年之后,我所经历的麦口是少乎其少的,心中所有麦口的记忆大都是当年的印象。老小时候的那种麦口场面,每每回忆起来,总觉得该用“热火朝天”这个词来形容。先是全村的男女劳力一齐出动,将麦子从田间请到麦场,当然了,这个“请”字是要付出些辛劳和汗水的。而后偌大的麦场才是真正的热火朝天。麦草铺满了场,就用驴子、骡子,也有牛,拉着大小不一的石碌一圈圈地轧麦草。赶牲口的多是些老把式,常常还会喊号嘹,有些悠扬高亢。那边其他人一样不闲着,有翻动麦草的,有收落下来的麦粒的。到最后,*把、掃子、扬场的锨一并用上,小山一样的麦堆就鲜亮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了。可惜分到各家各户的时候,却又少得可怜。乡亲们做煎饼不舍得全用小麦,就掺上些玉米、山芋干,也有掺一种叫做麦竹的草的,吃到嘴里拗口、难嚼,但能填饱肚子。
后来分田到户了,再到麦口,就是各家忙各自的,人人都更勤快了,天不亮就下田。父亲给我说过,这一者是大早凉快,再有就是要抢收的。麦口最怕连阴天,一旦遇上,就会遭遇“烂麦场”。那是每个乡亲最不愿看到的事,一季的收成不能坏在老天的手里,一样的要抢,赶在雨前把麦垛子遮盖好,把落下的麦子运到屋子里晾着,夏日的雨来得及时、去得也快,常常是转眼又现了太阳,等场面干了,就又要把屋里的小麦倒腾出来,很是累人。做这样繁重的体力活,吃食上也少有改善,我依然记得,母亲和所有乡间妇女一样,在麦口多是间或煮上几枚鸡蛋,父亲还常常舍不得吃,要让着给我。
现在又临麦口时节,心里牵挂着那农事,当然更是牵挂着父母,就一个电话打回了老家。我给父亲说,麦口大忙时节,却不能帮上忙,心里很是不安呐。父亲说,你还当是老早的麦口,现在不一样了呢,不忙的。
父亲这话我相信。先前村里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,每每到了麦口大都是要赶回家忙农事的,主要是收麦一直都没有摆脱手工的操作,只是在脱粒上机械化跟上了。收麦的机械算是大型机械了吧,但很少有人有购买能力。近两年,河南的一帮机械手瞅准了这个商机,每逢麦口都过来赚上一把,村里人也乐意让他们赚呢。父亲告诉我说,今年就更方便了,村西的小安子新买了一台收割机,镇上还贴了他两千块钱呢。还有现在的麦口,在农村里很有点像过节的意思了,家家都在冰箱里备些菜肴,生怕亏了自己的身体。我笑了,问父亲,当年人就不怕亏了自家的身体吗?还是条件不允许嘛。
父亲也笑。我说您老人家就多保重身体吧。父亲还是那话,不忙,没事的。
知道麦口不忙,收成不差,是好事情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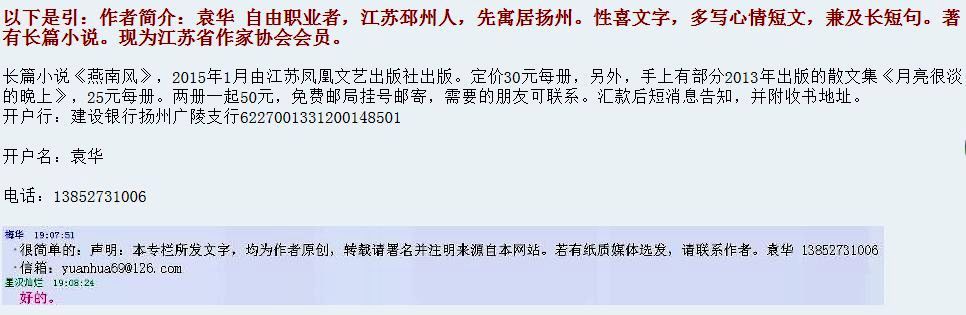
|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