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第二辑 闲情偶寄
下扬州
我的老家邳州,和扬州该算得上是大有渊源的,眼下,邳州的乡音几乎遍及扬州的每一个角落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曾在老家乡镇宣传部门的上报材料上,看到这样的文字:近几年来,我镇大批民工涌向扬州,以自由经营为主,形成了不小的市场,在当地号称“邳州一条街”…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,“下扬州”这样的字眼成了挂在乡邻嘴上的时髦话。
我最早接触“下扬州”这个特定的词组,当然是因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: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这寻常的七个字一搭配到一块,读起来不由你不心生一份唯美、生出一种向往。后来,又听到过一首民歌,叫《摘石榴》,当中也有下扬州的字眼,那样的下扬州却还是和爱情有着关联的。
古人下扬州,用舟车劳顿来形容当是最恰当不过的。其实,在早些年里,今人下扬州似乎也是不怎么便捷的。就说我邳州的乡党们吧,当年下扬州竟然也是用的一个“舟”字。
这个舟,自然就是船了,而那个“早些年里”则要追溯到30年前的。老张是我众多乡党里最早下扬州的一个。说起当年的往事,老张略显浑浊的眸子里,瞬间竟有些熠熠生辉。
老张说,当年下扬州,就是坐着船,一路顺流而下的。要坐船,只有县上才有码头。开往扬州的船,一大早,天还黑朦朦的时候就起锚了。这样,为了能赶上坐船,是要在县上住一宿的。头天里,老张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,步行50里路到县上,块把钱一宿的便宜小旅馆,老张也舍不得住,就睡在码头边简易的候船厅里,因为心有所牵挂,怕错过了上船的时间,通常里,到了后半夜,老张就睡不着了。
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声,船披着晨辉慢慢的离开了岸,向着那个叫扬州的地方驶去。那样的旅途是枯燥的,蜷缩在下等舱里,除了睡,就是吃,吃的东西是老张从自家带出来的大饼。老张清楚记得,自己一上了船,饭量就比在岸上明显地小了不少。
从当天的一大早开始,船在水上不停地航行,到了第二天的天黑,船才算到达目的地,那是个叫湾头的地方,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扬州,想进扬州城,还是要用双脚继续丈量的。
老张说,曾有好几个年头,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往来于老家和扬州之间的。后来,两地通班车了,但是为了省些路费,还是常常选择坐船,除非是有些特殊情况需要赶时间,才会去坐班车,当然了,多花些车票钱是不冤枉的,坐班车,当天就能到扬州。
时间到了1990年前后,随亲戚、跟朋友一道下扬州的邳州人越发多了起来,运输部门也看到其中的商机,就选了两个出行人员相对集中的乡镇作为定点,开通直发扬州的对点车次,这样,就给下扬州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。而后来京沪高速的建成通车,把邳州到扬州“朝发夕至”的时间段又给缩短了一半。
从京沪高速开通之后,老张就不怎么回邳州了。唯一的一次,还是坐儿子开的小车回去的,700多里的路程,儿子只用了3个半小时。老张说,这样算起来,从老家到扬州,一天跑个来回都不费事,感觉上比当年去县上还要快呢。这话不假,从村里到县上,50里地,步行是要好几个小时的。
或许上苍总是垂爱扬州的,终究不忍让扬州没有铁路。2004年4月18日,将永远载入扬州人的史册。这一刻,扬州人百年的铁路梦想终于圆了,烟花三月下扬州,从那一刻开始,下扬州的途径就又多了一条。
曾经的水路客运早已湮灭于历史的烟波中,孤帆远影只能长留在诗歌的意境里。公路与铁路的并驾齐驱并不曾满足“贪心”的扬州人,下一个梦想便是蓝天,扬州人要让飞机的轰鸣声划过二分明月城,带来五湖四海的宾客。
2012年5月8日是个值得扬州人大书特书的日子,这一天,千年梦想一朝得圆,骑“鹤”下扬州成了不争的事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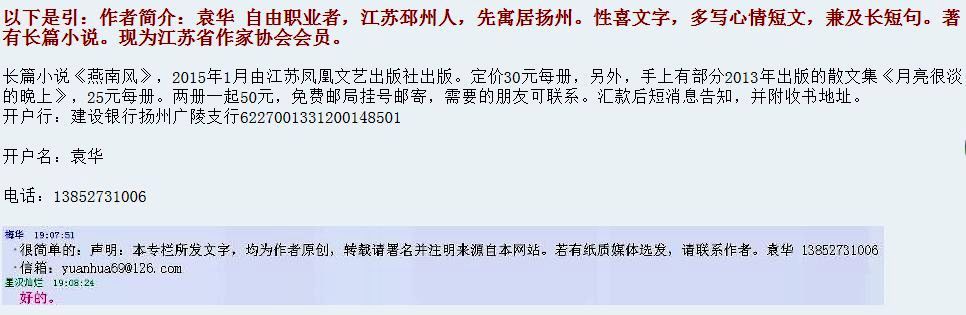
|

